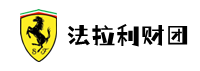邮编: 300009
电话:0571-98765432
传真:0573-12345678
网址: www.abcde.com
邮箱: boss@gmail.com
杏运娱乐-杏运娱乐注册登录平台-首页-风湿免疫病的治疗已经进入靶向时代回顾生物靶向药的研发历程中的英雄人物(主管:QQ66306964 主管:skype live:.cid.6c7b79dae5ec9830)新博2新博2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NCI)提供的生物药物的定义是“由活生物体或其产品制成的物质,用于预防,诊断或治疗癌症和其他疾病。生物药物包括抗体,白介素(ILs)和疫苗。也称为生物制剂”(/dictionaries/cancer-terms/def/biological-drug)。“生物制剂” 或生物反应修饰药物”在肿瘤和自身免疫病的治疗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慢慢扩展到其它医学专业领域。
用于临床治疗的药物以及源自生物的药物在医学中并不是新现象。Shibasaburo Kitasato(1852-1931)和Emil von Behring(1854-1917)最早发现“血清疗法”或“抗毒素疗法”。实际上,即使在今天,白喉,破伤风和狂犬病抗毒素仍在使用。产生这种血清的方法及其纯化过程不仅繁琐且耗时,而且由于人体对外来(动物)蛋白质的免疫反应而导致经常出现一种称为“血清病”的疾病。出血性疾病中使用的凝血因子和几种生长因子(用于血液学和其他学科)也是从生物学上衍生的。已使用数十年的较旧的胰岛素,也是一种生物来源的分子(来自猪的胰腺)。
随着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现在可以合成诸如胰岛素(以及其他几种包括促红细胞生成素)的物质,而无需涉及生物系统(例如细胞培养,转基因细菌和酵母细胞)。但是,如果治疗需要高度特异性的大量抗体(源自针对血浆中异常分子的抗体生成浆细胞的单个克隆),则需要所涉及的生物学过程有非常深入了解。现在,mAb被广泛用于治疗涵盖医学几乎所有专业领域的大量疾病。然而,当今很多医师可能尚未完全意识到在过去由一群热情的临床医生,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和药理学家组成的专门小组所做的开创性贡献和艰苦的努力才使这一切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生物学发展的故事是一群杰出的研究人员,尽管经历了几次令人心碎的失败,但他们最终成功地发现了一系列新的治疗分子,这些分子不仅改变了许多慢性“无法治愈”的治疗方式疾病,但也为“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线索。这些重大发现改变了当今医学的实践方式。
重现许多医学科学家的成功和艰辛,他们数十年来的敏锐观察和艰苦工作最终导致了对类风湿关节炎发病机理中的关键分子高度特异性的临床级单克隆抗体(mAb)的产生 (RA),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组织培养一直是细胞生物学研究的中心,特别是对于了解健康和疾病中的细胞功能。威廉·鲁克斯(Wilhelm Roux)是Rudolf Virchow(在实验胚胎学领域有终生贡献的德国医师)的学生,他是1885年在实验室中成功地成功培育出了雏鸡的髓质板的第一人。由美国生物学家和解剖学家罗斯·哈里森(Ross Harrison)开发的细胞培养技术在1907年被认为是第一个成功进行人工组织培养的研究。从1911年到1935年,组织培养技术达到了成熟的水平,这使其成为研究细胞生理和行为的关键。在此期间,其他几位专门的生物学家为使该技术更加人性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法国外科医生兼生物学家亚历克西斯·卡雷尔(Alexis Carrel)就是其中之一,他获得了诺贝尔奖(1912年),并开创了完美的培养技术。卡雷尔(Carrel)从1906年至1927年在洛克菲勒学院(Rockefeller Institute)工作,并与对癌症研究特别感兴趣的美国外科医生和病理学家Montrose Burrows(1911)合作。他们共同开发了体外细胞培养的长期无菌技术。Burrows是“组织培养”一次的创造者,最早将该技术应用于温血动物的组织研究。从风湿病学的角度来看,洛克菲勒研究所医院的Vaubel最早于1933年以组织培养的方式研究滑膜细胞。他首次对滑膜组织中两种不同细胞类型进行了描述,即成纤维细胞样滑膜细胞(FLS)和巨噬细胞样滑膜细胞(MLS)。
在20世纪初期开发用于长期细胞培养的技术时,很快就意识到收获的培养上清液提供了细胞分泌的分子的丰富来源。该观察结果导致大量研究定义了它们的生物学特性。发现其中大多数是小的蛋白质分子(〜5-20 kDa)。在没有统一的命名系统的情况下,不同的研究人员给出了不同的名称,同一分子通常使用两个不同的名称杏运娱乐-杏运娱乐注册登录平台-首页-。1974年,美国(New Yorker)生物化学家Cohen和198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及其同事创造了“细胞因子”一词来表示细胞培养液里物质。他们认为,体内许多非白细胞的细胞也可能产生细胞因子。严格地说,根据涉及的细胞类型,“细胞因子保护伞”除细胞因子外还包括趋化因子,干扰素(INF),IL,淋巴因子,TNF等。当时,人们推测这些分子必须参与细胞信号传导(细胞之间的“串扰”),因此可以被认为是影响邻近细胞的功能和行为的“短程”激素(自分泌型,旁分泌型)。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分子的术语仍在不断变化,并且已经流行了许多不同的名称,包括迁移因子,淋巴因子,单核因子,IL,趋化因子,自分泌型和副裂解型。这些也以发现它们的组织命名,例如神经因子,脂肪因子等。按照惯例,“细胞因子”一词不包括激素和生长因子。
为了研究健康和疾病中不同组织中的分子,通常使用在小型实验动物中产生的示踪抗体。但是,使用这些“多克隆”抗体缺陷就是特异性不够和批次间差异的问题。随着能够产生纯分子的DNA克隆技术的发现,这个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如果没有生产纯的分子和蛋白质的生物技术克隆方法等复杂的技术,就不可能进行高级的基础研究,从而发现用于临床的药物级生物制剂。一种用于生产特异性抗体分子的技术,该抗体均匀地(克隆地)带有相同的三维结构,例如,相同的重链和轻链,以及可变区和高变区以及相同的糖基化模式,与相同的分子发生完全反应特定抗原的抗原决定簇,“杂交瘤技术”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细胞因子的发现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结核病和结核菌素的研究得到了大力发展。Zinsser,Tamiya和Arnold Rich在1926-1927年关于结核菌素致敏组织释放的“通透性因子”的工作,可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细胞因子效应”的第一个明确证明。从1957年到1974年,几个研究小组报告了使用不同生物系统“刺激的”(致敏)细胞分泌的分子的研究结果。艾萨克斯(Isaacs)和林登曼(Lindenmann)在处理鸡胚绒膜尿囊膜中生长的活流感病毒时观察到,用热灭活的流感病毒预处理的细胞会抑制活流感病毒的生长。他们推测,这种现象是由绒毛膜尿囊膜细胞释放的蛋白质介导的,该蛋白质已用热灭活的流感病毒进行了预处理。他们将其命名为“干扰素”(干扰病毒的生长)。拜伦·瓦克斯曼(Byron Waksman)和马吉特·马托夫斯基(Margit Matolfsky)(1958)研究表明,巨噬细胞对结核菌素的致敏作用并没有引起损害,而是引起巨噬细胞活化(巨噬细胞激活),这是弗氏和麦克德莫特早期利用的一种佐剂,可增强对弱抗原的免疫反应。1966年,发现了抑制正常巨噬细胞迁移特性的迁移抑制因子。1968年,几个小组几乎同时发现了受刺激的淋巴细胞分泌的一种蛋白质,他们将其命名为“ lymphotoxin” ,后来又更名为“TNF-β” 。Dudley Dumonde(1969)被认为第一个使用了“淋巴因子,单核因子”这一术语。他将它们定义为淋巴细胞激活产生的细胞免疫的非抗体介体,可能指向先天免疫系统的淋巴细胞。1972年,伊加尔·格里(Igal Gery)在拜伦·瓦克斯曼(Byron Waksman)的实验室工作时,描述了一种“淋巴细胞激活因子”(LAF)。1974年后不久,科恩(Cohen)引入了上述“细胞因子”一词。确实,细胞因子的传奇充满了科恩和拜伦·瓦克斯曼的名字。前者获得了诺贝尔奖,新博2娱乐注册而后者则成为了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一位传奇的免疫学家。
除了包括生物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在内的基础科学家之外,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许多人都是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感兴趣的临床医生。此时,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几个新的专科:风湿病和临床免疫学。一些著名的名字包括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临床免疫学和风湿病学系。Charité风湿病和临床免疫学系-柏林大学医学院;UMC乌特勒支风湿病和临床免疫学;阿姆斯特丹风湿免疫学;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风湿病和临床免疫学等。对于那些从事该领域的人来说,RA由于相对容易获得关节以获取组织(病理性滑膜)以破译侵蚀关节中软骨和骨骼的滑膜炎和血管翳的发病机理。显然,滑膜组织最早是在组织培养中生长的关节组织,可以帮助更好地了解其在RA等疾病中的生理学和病理学。如前述Vaubel在实验室中成功培养滑膜组织的工作。
直到1960年代后期,人们一直在讨论RA的发病机理,从牙龈感染(该理论最近在牙龈卟啉单胞菌中被认为可能是罪魁祸首的复兴)到由酶,酶原和可能自身的改变引起的异常细胞外基质(ECM)活化,暴露出ECM的改变的抗原从而引起自身免疫。需要提醒的是,1962年,间质胶原酶(现在称为金属蛋白酶-1或MMP-1)及其改变组织结构的特性已经被发现。当时,“异常的细胞外基质”的疾病已被翻译为“胶原蛋白疾病”,我们今天将其称为系统性免疫炎性疾病(两类:自身免疫性炎性疾病和自身炎性疾病)。但是,酶学的进步(1970年代至1980年代)及其在RA中的应用反驳了改变的酶在ECM损伤中的任何直接作用。人们不得不回到“类风湿滑膜细胞”,特别是对于关节破坏过程至关重要的血管醫。但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血管醫中的细胞(免疫细胞,炎性细胞)如何对ECM造成损害?”
1974年,来自瑞士日内瓦大学医学院的Dayer等加入了以克雷恩为首的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著名的关节炎科。在这里,Dayer及其同事研究了RA患者的滑膜培养物,发现滑膜成纤维细胞能够产生大量胶原酶和前列腺素E2(PGE2)。他们证明滑膜成纤维细胞与单核细胞的物理接触对于加速胶原酶和PGE2的产生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该过程逐渐变得自治(开始表现得像肿瘤细胞)。他们成功地纯化了一个小的15 kDa分子,作为滑膜成纤维细胞的增敏剂/刺激剂,产生了大量的胶原酶和PGE2。该分子被称为“单核细胞因子”或MCF。根据详细的色谱研究,MCF在1979年于瑞士Ermatingen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淋巴因子研讨会上被重新命名为IL-12。再次,在分析单核细胞亚群的各自功能时,Nardella等证明了T淋巴细胞刺激的单核巨噬细胞(MΦ)产生了MCF,从而建立了从TL→MΦ→滑膜成纤维细胞活化的顺序途径,在此直接物理接触单核细胞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在 40 y之后,RA中关节疾病的这一范例仍然成立。
体液免疫反应(B细胞受累)的贡献后来被添加到方案中,表明自身反应性IgG同种型类风湿因子可直接刺激MΦ,从而激活滑膜成纤维细胞,而无需T细胞。Seckinger等还发现了第一个IL-1受体拮抗剂(IL-1Ra),随后描述了天然细胞因子拮抗剂如何阻断同一家族中另一种细胞因子的结合。因此,开发了在受体水平上IL-1抑制剂与IL-1的竞争性结合测定的原理。该发现对1990年纯化并克隆IL-1Ra的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生物技术公司Synergen的研究人员至关重要。1980年,IFN-α和IFN-βcDNA以及T淋巴细胞(TNF)的克隆-β),TNF-α和IL-1分别于1984年和1990年获得IL-1Ra。这些发现是非凡的发现,自那时以来,重组分子和特异性mAb彻底改变了信号转导领域,根据疾病类型和治疗方法对不同细胞因子的层次进行解剖。Dayer等人的一项重要发现与RA中滑膜成纤维细胞的行为有关。正如已经提到的,他表明暴露于MCF的正常滑膜细胞表现出惊人的形态变化,在空间结构改变的情况下变得细长,并开始产生大量的胶原酶(MMP-1)和PEG2。这种修饰的细胞称为滑膜成纤维细胞。新博2娱乐更重要的是,Croft及其同事证明,在持续暴露于MCF一段时间后,滑膜成纤维细胞的这种亚群切换为细胞生长的自主模式,并证明了不同基因的表达和对不同细胞因子的响应模式不同。Dayer如此出色的工作促进了后来涉及抑制MCF(后来更名为IL-1)的研究,但是在控制类风湿性疾病中没有显现明显的效果。
关于术语TNF的发现和创造,生物学家之间存在一些困惑。事后看来,这种混乱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历史上,是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Carswell等人在1975年在享有声望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他们的开创性工作。使用了肉瘤Meth A模型和其他由内毒素引起的肿瘤模型,他们证明了用诱发网状内皮系统非特异性增生的物质(例如BCG,酵母聚糖,棒状杆菌)引发的小鼠释放的物质可引起出血性坏死,模仿内毒素本身的作用。他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肿瘤坏死因子”或仅仅是TNF,还不是最好的名字。这是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名称。作为小鼠的实验性发现,它未能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恰好10年后,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Beutler等人(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纪念堂的劳埃德·奥尔德实验室的对面)首次发表了TNF在疾病发病机理中的重要作用的证明。第一作者Bruce Beutler与Jules A. Hoffmann因“他们关于激活先天免疫的发现”而分享了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切拉米(Cerami)建立了一支由杰出的生物学家和免疫学家组成的团队,该团队除Beutler之外,还包括著名的瑞士科学家让·米歇尔·戴耶(Jean-Michel Dayer)(他的工作已在上文中进行了描述),这一成就必须得到赞扬。该小组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描述了由内毒素诱导的RAW 264.7细胞分泌的一种脂蛋白脂肪酶抑制激素,他们将其命名为“ cachectin”。然而,他们还提到了同一分子的名字TNF。该论文在劳埃德·奥尔德实验室(Lloyd Olds Laboratory)报告并描述并使用“ TNF”一词的10年后才出现。公平地说,对于Beutler及其同事来说,他们在1985年的这篇论文中同时使用了术语cachectin和TNF。
大多数有价值的工作都需要一些灵感,很多汗水和一点运气。切拉米(Cerami)的主要工作是关于“被忽视的热带病”,为此他经常前往非洲,以肯尼亚为基地。在那里,他对由采采蝇传播的原生动物,布鲁氏锥虫引起的患有非洲昏睡病的牲畜产生了兴趣。他确定这些牛的血液中携带一种导致疾病的分子。对该分子的进一步研究导致“ cachectin”的发现。有人认为,如果施用针对恶病质的中和抗体,恶病质(以及恶病质的其他不良反应)可能会逆转。然而在他在肯尼亚的实验中,向患有“昏睡病”的牛施用了抗Cachectin抗体,导致其死亡。失败的实验使塞拉米感到非常失望。恶病质治疗中,Cachectin / TNF抗体的失败成为后来包括Ravinder Nath Maini和Marc Feldmann在内的几位研究者的主要绊脚石,当时他们希望在针对另一种疾病即RA的人体试验中使用少量针对TNF的mAb 。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不同意在人体中开展临床试验。mAb作为治疗剂的声誉受到了打击。
TNF的发现引起了世界各地基础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的想象。Jan Vilček在2008年巧妙地强调了Beutler及其同事在TNF方面所做工作的重要性。并可能和RA等疾病发病机制有关。
TNF的纯化和cDNA克隆:1984年12月在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举行的25位科学家会面-Lloyd Old和JanVilček脱颖而出
Vilček1958年在布拉迪斯拉发(位于老捷克斯洛伐克)刚刚医学毕业,当时他参加了INF的共同发现者Alick Isaacs和以开发活脊髓灰质炎疫苗而闻名的Albert Sabin的会谈。他变得很有动力,并开始从事INF领域的工作。还在布拉迪斯拉发时,他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发表了一篇关于INF的出色论文。1964年,他从捷克斯洛伐克移民到美国,并以助理教授的身份加入了纽约大学(NYU)医学院,以完成他对生物系统高级基础研究的热情。1982年,他的团队已经对INF进行了深入研究,描述了两种类型的IFN-α和IFN-β(现称为I型INF)。在当时流行的费力细胞培养方法由单核细胞产生这些INF的过程中,他的团队观察到了另一种分子,称为“免疫INF”(或称为INF-γ的II型INF)。进一步分析,有两种不同的分子;一种由淋巴细胞产生,另一种由单核细胞产生。1984年,他的团队将前者命名为“淋巴因子”(也称为TNF-β),而将后者命名为“单核细胞衍生的细胞毒素”,后来变成了经典的TNF,现在称为TNF-α。这是一项独特的工作,涉及来自美国三个不同实验室的九名科学家(纽约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纽约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发育性造血实验室;纽约基因科技公司蛋白质生物化学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旧金山)。1984年12月,劳埃德·奥尔德(Lloyd Old)及其同事在斯隆·凯特琳纪念癌症中心纪念馆举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对TNF和淋巴因子感兴趣的科学家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它包括上述论文的几位作者,包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基因泰克公司蛋白质生物化学系的Bharat Bhushan Aggarwal。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Bharat宣布了他的同事在Genentech上对人类TNF的第一个完整氨基酸序列,人类淋巴毒素蛋白和cDNA序列的部分序列,TNF的染色体位置和淋巴毒素结构基因的开创性工作。自那次历史性研讨会以来,Vilček与Genentech建立了积极的持续合作关系,其中包括与Bharat Aggarwal和David Goeddel的合作,后者提供了重组人TNF的纯净形式的样品。这极大地促进了在维尔切克实验室中了解TNF的生物学功能和作用机理的研究。直到那时,关于TNF-α的唯一已知信息是它们对某些慢性感染动物的肿瘤和恶病质的细胞毒性作用。为了破译TNF的生物学作用,研究不同的细胞以找出哪些细胞表面具有特定的高亲和力结合受体至关重要。维尔切克实验室中有两种容易获得的人细胞系:(i)HeLa细胞,一种永生的宫颈细胞瘤细胞系(HeLa细胞系是人类中最常见最古老的人类细胞系之一,来自于死于1951年的一名宫颈癌患者,并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中广泛使用。)(ii)在Vilček的实验室中生长的人二倍体成纤维细胞FS-4株。这些细胞显示表达有TNF的高亲和力受体。Vikcek实验室中的进一步实验表明,INF-γ通过增加TNF受体的表达来协同TNF的细胞毒性作用。就人类二倍体FS-4成纤维细胞而言,即使暴露于纳摩尔浓度的TNF,也会导致细胞形态发生惊人的变化,即使在光学显微镜下也能观察到。成纤维细胞随着其空间方向的变化而变长。Vilček实验室的一名学生,Vito Palombella发现即使在暴露于TNF的正常人成纤维细胞中,也表现出相似的形态变化。Lin和Vilček还表明,与其他生长因子一样,TNF导致人成纤维细胞中c-Fos和c-Myc mRNA的表达增加。他们随后的工作表明,TNF诱导了不同人类细胞中的大量基因,并且还是该分子的强力诱导物,后来被人们称为IL-6,它是包括急性期反应物在内的炎症的强力诱导物。
如果不提及传奇的1970年代至1980年代全美国临床免疫学家和自身免疫专家的“大师”临床免疫学家,物理学家,纽约洛克菲勒学院的亨利·昆克尔(Kunkel-girls)的故事,就不可能完成关于发现用于临床用途的生物制剂的故事。1951年,他做了一个独特的观察,即从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骨髓中收获的恶性浆细胞不仅具有完整的抗体制造机制,而且所有细胞在每个测试参数中均产生相同的抗体分子。这些患者的血清电泳显示为“单克隆(M)峰”。因此,骨髓瘤被认为是“单克隆同性恋病”之一,而骨髓瘤细胞系成为研究抗体的主要来源。迈克尔·波特(Bethesda NCI的分子生物学家)的偶然发现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简单,他在1962年报告称,在特定小鼠品系(BALB / c)的腹膜腔内注入矿物油会诱导骨髓瘤的生长。他的实验室为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几系骨髓瘤细胞。通过建立Kengo Horibata和AW Harris(在圣地亚哥著名的Salk研究所的Melvin Cohn的监督下)的体外培养技术,这些细胞的繁殖变得更加容易。这些细胞使用针对每个克隆的不同重链和轻链以克隆模式连续产生抗体。但是,无法确定这些抗体的确切特异性。确实,从十亿种可能的抗原及其表位中确定其特异性就像在大海捞针中找到一根针。当时大多数研究人员所想到的主要问题是:“是否可以将这些永生的骨髓瘤细胞系的克隆抗体生产机制重定向到单一特定表位的抗体上?”这样一来,可以解决纯化由马或小型实验动物产生的多克隆抗体的所有困难,并使它们相对特异性地针对细胞和分子进行定向研究。
1970年代,抗体和产生抗体的细胞(后来称为B细胞)领域的大多数研究人员已经认识到,骨髓瘤细胞系中仍然保留抗体的特异性可以使产生大量对特定抗原具有特异性的抗体的首要需求成为可能。从事这项研究的知名人士包括约瑟夫·辛科维奇(Joseph Sinkovics),布里吉特·伊塔·阿斯科纳斯(Brigitte Ita Askonas)和诺曼·克林曼(Norman Klinman)。
Sinkovics是得克萨斯州M.D. Anderson医院和肿瘤研究所的匈牙利免疫学家,于1970年将脾脏浆细胞与小鼠淋巴瘤细胞成功地自然融合。尽管分泌的抗体具有高度特异性和功能性,但其工作未能引起细胞融合领域其他人的想象。使用“杂交瘤”一词的功劳归功于Sinkovics,他产生了一种杂交细胞,该杂交细胞能够产生mAb,并具有恶性细胞的永生性。
Brigitte Ita Askonas出生时是奥地利人。但是,随着纳粹势力的增强以及在巴黎短暂停留后,她移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在麦吉尔大学担任研究人员,并获得了生物化学学位。在瑞士巴塞尔免疫研究所任职后,她搬到英国剑桥大学,在那儿攻读博士学位。她于1952年移居伦敦米尔山(Mill Hill)的国家医学研究所,并在化学部门工作至1989年。她对体内抗体合成的研究感兴趣。在处理骨髓瘤细胞的过程中,通过对Kunkel在1950年代的工作背景的了解以及她自己在生物化学领域的丰富经验,她是第一个阐明在产生抗体的浆细胞内合成免疫球蛋白分子的生物化学步骤。她也是第一次证明了一个单一的抗体生成细胞克隆产生的单个(单克隆抗体)类型的抗体,为此她1973年被选为皇家学院院士于。她提出了一些其他与抗体异质性有关的开创性发现。从历史上看,她是第一位在实验室生产mAb的科学家。对于这项工作,她使用了遗传上相同的受辐照小鼠来生产mAbs。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她的作品未能得到应有的认可。一个可能的原因可能是这些产生抗体的克隆易碎,无法存活足够长的时间用于批量生产mAb。
美国免疫学家诺曼·克林曼(Norman Klinman)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与Wistar研究所联合,于1969年发表了一项技术,他将其称为“单焦点抗体” 。他使用了放射过的小鼠,这些小鼠注射了具有产生抗体能力的新鲜细胞,其中一些“归巢”在脾脏中。将该脾切成小方块,并放入含有特定抗原的组织培养物中。假设是含有特定抗体产生细胞的脾脏片段会产生对该抗原具有特异性的抗体,然后可以从培养物上清液中收获这些抗体并用于实验。
尽管Niels Jerne(巴塞尔免疫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并未直接参与治疗性mAb(生物疾病修饰药物或bDMARDs)的开发,但他的抗体特异性“自然选择理论”使他跻身于免疫学领域最聪明的人之列。他与科勒和米尔斯坦分享了1984年诺贝尔奖,这是因为他们在理论和实践对塑造我们对人体免疫系统的理解方面的重要贡献。耶恩(Jerne)的溶血菌斑技术(在软琼脂板上)是研究单个mAb产生细胞及其生物学的绝佳方法。该技术被广泛用于研究产生的抗体的单克隆抗体和特异性。
阿根廷生物化学家塞萨尔·米尔斯坦(CésarMilstein,1927-2002年)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并于1956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英国文化协会的资助下,他于1958年移居英国,成为一名入籍英国公民,并加入了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生物化学系。他还曾在医学研究理事会(MRC)任职。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研究围绕着令人着迷的抗体多样性及其产生机理。在今天的免疫学家的激烈辩论中,“种系”与“体细胞突变”理论确实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时候,基于简单的常识,著名的美国分子生物学家约书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于1959年主张将体细胞突变作为抗体多样性的基础,因为否则自然界不会浪费无数的基因,而只能生产各种各样的抗体。此后不久,Brenner(哈佛大学)和Milstein(剑桥大学)发表了著名的“ Brenner-Milstein模型”,用于抗体多样性的产生。
1970年代初,来自澳大利亚的博士后研究员Dick Cotton加入免疫遗传学研究,他加入了米尔斯坦实验室(Milsteins Laboratory),并一起完善了使用多种骨髓瘤细胞系的细胞融合技术。该技术涉及使用灭活的仙台病毒,该病毒是他从隔壁的实验室的亚伯拉罕·卡尔帕斯(Abraham Karpas)获得的,他使用后者来促进细胞融合。1973年,米尔斯坦(Milstein)在巴塞尔免疫研究所(Niels Jerne担任该研究所所长)介绍了他们在骨髓瘤细胞融合方面的工作。观众中有一位年轻的德国生物学家乔治·科勒(GeorgesKöhler),他正在从弗莱堡大学读博士学位。由于米尔斯坦的工作而激动,科勒(Köhler)于1974年4月加入他在剑桥的研究团队,担任博士后科学家,以推进抗体多样性的研究。为了证明超突变理论,他们需要永生的产生抗体的细胞系。到这个时候,米尔斯坦已经获得了波特的小鼠骨髓瘤细胞系(MOPC21),霍里巴塔和哈里斯曾在1970年代初使用该细胞建立长期组织培养。Milstein与Brownlee合作,能够建立骨髓瘤细胞系。
到科勒加入米尔斯坦实验室时,杂交瘤技术已在全球多个实验室中确立。然而,这两个努力寻找一种必须具有三个基本特性的杂交细胞:(i)诱导不朽以合成抗体分子,(ii)它必须具有产生单个抗体分子的特性,即特异性mAb ,并且(iii)它应该能够在组织培养物中无限期地生长。使用从绵羊红细胞免疫的小鼠脾脏碎片中分离出单个抗体形成细胞的技术(上述克林曼技术),以及由迪克·科顿和亚伯拉罕·卡帕斯在实验室中完善的,已建立的仙台病毒细胞融合技术(在熟练的技术协助下)由雪莉·豪(Shirley Howe)提供的产品,科勒(Köhler)和米尔斯坦(Milstein)成功地产生了“杂交瘤”,这种杂交瘤可以制备针对绵羊红细胞某些抗原的单克隆抗体。有了这样积极的成果(通过使用Jerne溶血斑技术证明),这两位生物学家突然意识到他们已经成功地发现了其他人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制作的一种工具。用严格的科学术语来说,他们开发了一种永生的抗体生产细胞系,该细胞系能够无休止地供应已知特异性的相同抗体。该方法很快以“杂交瘤技术”的名称流行。由此产生的抗体称为“ mAb”,表示它们源自单个杂交细胞。柯勒(Köhler)和米尔斯坦(Milstein)因此在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与尼尔斯·耶恩(Niels Jerne)分享了这一发现,尼尔斯·耶恩(Niels Jerne)在提出发现之前已有了理论框架。尽管这些杂交瘤可以无限期地大量繁殖,但是由于米尔斯坦实验室中仙台病毒的供应减少。幸运的是,最近加入米尔斯坦(Milstein)的博士后乔凡尼·加尔弗雷(GiovanniGalfré)通过使用聚乙二醇(PEG)解决了这一问题,聚乙二醇已成功用于其他细胞-细胞融合实验中。Galfré引入PEG大大增强了杂交瘤技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生成永生的mAb。与传统的多克隆抗体相比,mAb的发现预示着重大进展。
1975年,米尔斯坦(Milstein)在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RC)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介绍了他在杂交瘤技术上的研究成果。受过训练的科学家托尼·维克斯(Tony Vickers)在MRC行政部担任官员。他意识到了这项发现的巨大商业价值,因此向美国国家研究发展公司(NRDC)发出了警告,该公司负责为MRC发明申请专利。令MRC政府失望和惊讶的是,NRDC的答复相当令人沮丧:“对于我们来说,要确定可作为商业企业进行的任何直接实际应用肯定是困难的,……而且目前尚不清楚自然论文中目前拥有哪些专利功能”。事后看来,对杂交瘤技术的这种错误判断可能导致英国经济损失数十亿美元!
在最初的日子里,研究人员非常重视科学伦理,关于发现的商业开发的任何想法都被认为是“罪恶的”。实际上,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之间可以自由交换思想/想法和研究方法,而不必担心知识产权、方法学和著作权。在这样一种自由交换思想和材料的科学氛围中,米尔斯坦于1976年9月收到了在费城Wistar研究所工作的科学家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Hilary Koprowski)的要求(该大学成立于1892年,自1972年起成为纽约大学附属于NCI的癌症中心)。本着“科学自由交流”的精神,米尔斯坦立即向科普罗夫斯基提供了一个杂交瘤细胞系。Koprowski(1913-2013)是波兰科学家,他是口服脊髓灰质炎和现代狂犬病疫苗开发的先驱。在发现单克隆抗体的历史中,提到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Hilary Koprowski),卡洛·克罗斯(Carlo Croce)和沃尔特·格哈德(Walter Gerhard)被授予两项专利(1979年10月和1980年4月),以生产抗肿瘤和流感病毒的单克隆抗体。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家获得生产mAb的专利。几乎同时,科普罗夫斯基还共同创立了Centocor,这是首批商业化生产用于诊断和治疗的mAb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Remicade(英夫利昔单抗),用于治疗RA的第一种生物制剂]。遗憾的是科勒和米尔斯坦的贡献没有得到承认。可以说,1970年代是英国政治和经济忧虑的日子。未能获得如此重要发现的专利引发了该国的政治风暴,最终到达了时任总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办公桌。至少可以说,她很生气;英国错失了良机。
Vilček对开发针对TNF-α的英夫利昔单抗(infliximab)做出了巨大贡献,英夫利昔单抗是第一种可用于人类的治疗方法。上面已经描述了很多事情,以及宾夕法尼亚州马尔文的Centocor实验室的故事,以及Kapowski在Centocor的角色。Centocor的创始人兼未来总监Michael Wall通过与一家从事IFN-β(旧名称淋巴毒素)研究的小型生命科学公司的早期合作而为Vilček所熟知。1983年他们正在为新公司的发展计划寻求学术界的智力支持。经过讨论,人们产生了通过科学合作产生不同mAb的想法,该公司将在商业上加以利用(可能是在开发利用mAb的酶联免疫测定法中)。值得注意的是,Vilček还提到了它们可能在人体中的治疗用途。因此,达成了一项便利的财务安排,其中Vilček的实验室将生产单克隆抗体,而Centocor将对其进行商业开发并作为回报,将补贴授予Vilček的实验室,并向纽约大学支付特许权使用费。mAb技术专家Junming(Jimmy)Lee受到了Centocor资助。他在Vilček的实验室生产了首个抗人IFN-γ的单克隆抗体。到1980年代后期,Centocor希望实现单克隆抗体的治疗用途多元化。在1980年代中期Cerami及其同事研究TNF在细菌性败血症中的作用以及Vilček实验室和Centocor的几位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产生了针对人类的人鼠嵌合mAb(称为cA2, 1990年代初期的TNF)。但是,它在败血病患者中未产生任何临床积极效果,因此未获得FDA批准。1993年,伦敦肯尼迪风湿病研究所的两名科学家(RN Maini&M Feldmann)向Centocor提出了部分抗人TNF的cA2 mAb的申请。Centocor成为市值十亿美元的公司,Maini和Feldmann的工作开启了靶向药物的全新时代。
维尔切克博士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350多篇论文,并拥有46项美国专利。他撰写了《爱情与科学:回忆录》,于2016年出版。Jan T. Vilcek和他的夫人马里卡(Marica)是纽约大学医学院的主要捐助者,以及2000年成立的维尔切克基金会(Vilcek Foundation),以表彰和提高人们对移民对美国科学,艺术和文化的贡献的认识。
2020年维尔切克生物医学科学奖授予了出生于中国江苏的哈佛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家庄晓薇,以表彰她在超分辨率和基因组规模成像方面的工作。
英夫利昔单抗在临床医学中的首次使用-Maini和Feldmann的贡献。
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肯尼迪风湿病研究所的Maini等人和Feldmann和Basten注意到组织培养的免疫细胞上清液具有显着的生物学活性。当时的技术还不足以深入分析这些上清液中的分子。到1970年中期,反映了任何天然产生的分子的mRNA的cDNA克隆技术变得可用,这简化了健康和疾病组织中细胞因子的研究。Maini是风湿病学家和免疫学敏锐的学生,与Feldmann联手对RA中的滑膜组织和细胞因子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关节置换手术,风湿病科经常进行穿刺活检和频繁的关节穿刺。这使得他们的工作更加轻松,因为他们可以轻松获得病理性滑膜组织的样本。自Vabuel的开创性工作以来,此时已经建立了滑膜组织培养技术。通过局部修饰,Buchan等和Feldmann等可以通过mRNA表达研究RA患者滑膜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的作用。他们在培养上清液中观察到了一系列炎症细胞因子,包括TNF,IFN-γ,IL-1,淋巴毒素,IL-6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GM-CSF)因子。有趣的是,滑膜细胞具有连续产生细胞因子的能力,这与大多数细胞因子在正常生理过程中的短暂出现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现象被称为“细胞因子生产失调”(暂时性生理与连续病理性生产)。与FLS发布的先前有关滑膜组织细胞因子的研究(Dayer,1976-前面已详细提及)不同,Maini和Feldmann使用经酶处理的滑膜细胞,该滑膜细胞可以在培养物中存活长达一周。这项新技术使他们能够更详细地研究细胞因子失调和过度生产。到这个时候(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几个实验室已经针对大多数已知的细胞因子产生了mAb。例如,迈克尔·谢泼德(Michael Shepard)在美国基因泰克实验室(Genentech Laboratories USA)产生了针对TNF的mAb,他慷慨地将其提供给Maini和Feldmann进行研究。使用这种抗TNF的中和抗体,后一组研究人员观察到最不寻常的现象,即阻断TNF抑制了细胞培养物中几种其他重要促炎细胞因子的合成。这导致了一个关键概念,即TNF是RA发病机理中一系列炎性细胞因子的“顶点”。这些发现发表于1989年的开创性论文中,其第一作者是该团队的博士后研究员Fionnuala Brennan。这一发现的含义令人震惊。靶向单个细胞因子可完全抑制RA滑膜组织中的炎症级联反应。理查德·威廉姆斯(Richard Williams)博士生使用仓鼠抗小鼠TNF(Bob Schreiber提供),在小鼠中提供了概念证明,即给予抗小鼠TNF抗体可缓解胶原蛋白诱发的关节炎。下一步显然是在RA患者中使用抗人TNF抗体启动临床试验。
尽管有科学证据显示抗TNF抗体可抵抗小鼠的内毒素休克,但Cerami的在非洲的牛昏睡病实验中未获成功,却使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仍警惕地提供其抗人TNF单克隆抗体用于人体临床试验。这是Maini和Feldmann在寻求测试抗TNF mAb在RA中的功效时面临的主要绊脚石。幸运的是,费城的Centocor公司与纽约大学Vilček小组合作,对生产用于ELISA测试试剂盒和治疗人类疾病的mAb感兴趣。他们聘请Maini和Feldmann的前任学生James N. Woody担任Centocor的首席科学官,这为针对10名RA患者的小型临床试验提供了抗人抗TNF mAb的便利。1992年5月开始进行的研究产生了惊人的结果。患者表现出明显的临床改善以及炎症的减轻,即急性期反应物迅速恢复正常。1992年9月,马克·费尔德曼(Marc Feldmann)在以色列阿拉德(David Naor)举行的小组会议上公开宣布了Centocor抗TNF mAb的巨大成功,命名为“英夫利昔单抗”,并发表了结果。快速连续进行的几项临床试验证明了英夫利昔单抗治疗RA的疗效:该药物阻止了新的关节侵蚀的出现,并且一些现有的侵蚀开始愈合。以前任何用于治疗RA的药物都从未见过这种效果。
过去,大多数值得注意的科学发现都是偶然的,在科学家的生命中常常出现“尤里卡时刻”,但近年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例如,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圣玛丽医院医学院的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s)实验室的窗户隔夜打开。第二天早上,弗莱明(Fleming)在细菌培养板上看到了一个干净的小光环。光环的中心是产生青霉素的真菌Notatus notatus。这就是发现抗生素的方式,弗莱明因发现而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奖(与Chain和Walter分享)。从早期开始,就发生了从“经验”到“机械”方法的重大范式转变,其中研究了异常/失调的疾病机理,将为失调正常化所要达到的最合理目标归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了一种循序渐进的新技术,生理学中的新分子途径,新的调节通路,调节细胞和分子功能的新可能性。利用这一背景知识和病理(疾病)过程中涉及的步骤,可以确定治疗目标,并开发出针对那些分子的药物。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单个人为开发具有深远影响的药物所做的努力,这是前所未有的。凭着合理的推理和可靠的科学依据,首次记录使用该药物的临床医生通常是该药物的发现者。英夫利昔单抗的发展故事就是这种药物发现的典型例子。数十位敬业的科学家在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生物技术的不同领域进行了数十年的工作,这使得开发针对TNF-α的医学级mAb成为可能。由Mani和Feldmann领导的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风湿病学家-免疫学家团队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不仅因为他们开创性的发现TNF-α是细胞中炎症细胞因子级联的中心。RA的发病机理,但也将成为第一个在临床上实际使用它的方法,并证明其任何治疗方法都未曾见过的高效。
英夫利昔单抗的治疗成功为单克隆抗体在医学上的临床应用打开了大门,并极大地推动了制药公司开发针对多种疾病的其他靶向疗法。英夫利昔单抗对RA患者具有高疗效的公开声明引起了许多生物技术公司的想象。现在,他们可以将注意力从灾难性的感染和败血性休克转移到已经证明细胞因子网络失调的疾病,例如RA,脊柱关节炎和其他类似的全身性免疫炎性疾病,包括炎性肠病,银屑病关节炎和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在最近十年最畅销的10种药物中,至少有一半是mAbs。当今大多数医生可能都不知道,用于治疗用途的mAb的发现者是伦敦肯尼迪风湿病学院帝国学院的风湿病学家,免疫学家和临床医生。由于对科学和医学的杰出贡献,Maini获得了多个奖项,包括Crafoord奖(2000年),Albert Lasker临床医学研究奖(2003年),Paul Janssen博士生物医学研究奖(2008年),盖尔德纳基金会国际奖项(2014年),马克·费尔德曼教授获得Crafoord奖(2000年),阿尔伯特·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2003年),EPO欧洲年度发明家奖(2007年),保罗·詹森博士生物医学研究奖(2008年),恩斯特·先灵奖(2010年)和盖尔德纳基金会国际奖(2014年)。